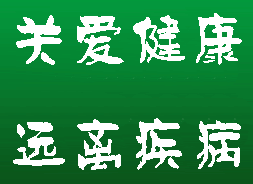散文工地女人
医院订阅哦!1建筑工地的打桩通宵达旦,不知疲倦地发出“嘭——”“嘭——”“嘭——”的震撼声,扩大着夜空的深度和广度,仿佛温柔的母性大地,正无力地躺着,默默地承受着人类与之交配的强大深入,这种深入的灼热与伤痛,在粘稠污浊的空气里,构成了我常常夜不能眠的巨大深渊。深渊里无声涌动的黑色波涛:是爱?是恨?我说不清楚。我搬家几次,都与建筑工地为邻。我在建筑工地的夜空中走过,就像走在一位苦难母亲的子宫里。逼人的热度。逼人的强光。逼人的潮湿与混浊。逼人的沉重与单调。都熔铸到新挖的大堆的黄土里,大坑的泥浆中,被彻夜不息的机器挖掘声、搅拌声覆盖着,被夜空下的巨大灯光炙烤着,充满了灼热的气息,但又是伤痛的气息。我睡不着。一个又一个窗前月下,我看见夜空下炫目的灯光污染着柔美的月色,将挖掘声、搅拌声炙烤成明晃晃的刀子,切割着大堆的黄土,大坑的泥浆与沙子,发出尖利的声音,子弹一样消失在我身体里最柔软温暖的地方。一个又一个风雪晨昏,我听到打桩的声音持续着,对着温柔的母性大地,“嘭——”“嘭——”“嘭——”地强力深入,仿佛深入到我的身体里,让我感到了浑身的撕裂与苦痛,我只能像哑女一样隐忍着,咬紧着滴血的牙关。夜空无边无际,隐忍深不见底。我一次又一次地搜寻着建筑工地上的施工者,总是难于发现他们活动的身影。他们哪能被轻易发现呢?他们活成了泥土的颜色,斑驳着汗浸过多少次的灰色衣裤,斑斓着泥糊过许多次的橘色帽盔,浸泡着那永远比泥浆更泥浆的手和腿,连洞开的牙齿也在被烘烤熟了的脸上呈现出苦黄的烟火颜色。我能够搜寻到他们的只有两点:有时,他们会在太阳落山的时候坐在砖头或水泥板上吸着劣质的纸烟,在清风拂过了他们黝黑的肩背、黝黑的脸膛的上空,吐出灰黑的烟圈,却是分外地优雅。烟圈在空中摇曳成飞天的龙,或者高飞的鹰,然后有星光的闪烁,却不知在他们的眼底还是在天上。他们默默无语的目光里,浓缩了黑夜与白昼的光芒,不怕风吹雨打和烈日的炙烤,总是黑白分明着,传递着他们的真情。当他们在泥浆中移动,在机器旁摇晃,在脚手架上爬上爬下的时候,又很快成为泥土的一部分,钢筋水泥的一部分,机器的一部分。我很难分辨出他们,也听不见他们作为人发出的任何声音。即使发出过什么,也被水泥与沙子的搅拌声、打桩声等等吞噬了。他们只是作为建筑工地上的一粒土块、一滴泥水、一缕灯光、一部机器的零部件存在着。但他们的力量又是强大的。我看不到他们的时候,建筑工地便是死寂的深渊;我看见了他们的时候,建筑工地便焕发出奇异的生机。2建筑工地是不分白天与黑夜,也不分春夏与秋冬的。春天来了,光秃的树干穿上了时髦的绿装,田间、山野或绿绒镶边的路也特别爱俏地花枝招展起来,空气中弥漫着泥土与花香的醉人气息。我就想,那个高鼻子大眼睛而有点像个外国人的高高的小伙子,立在打桩机旁,也像给高楼打桩一样,为自己的青春找到了一个坚实而又柔软的地方,打进了自己的爱与情吗?他面对的只是大堆的黄土、大坑的泥浆的建筑工地,也有盎然的春天吗?春天里,蝴蝶陶醉,舞出百花的怒放;蜜蜂歌唱,饱饮花蕊的蜜汁。小伙子也有停落的花枝、吮吸的花蜜吗?大自然的力量是伟大的,人心的春天随着季节的交替到来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小伙子吹起了轻快的小调:“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月亮走我也走……”不戴头盔的时候,他的浓密的头发不再被汗水濡湿又蒙着灰土乱贴在头皮上了,而是蓬松着野草疯长的气息。稍后,染了一头金发的他,更像个外国人似的。清晨,太阳还没有出,他的每一根头发仿佛已放射出朝阳的光辉;傍晚,太阳落下山了,他的每一个表情还会洋溢着晚霞的灿烂,虽然他满身的泥土还是泥土,满身的汗臭还是汗臭。当他停下手里活儿的时候,吸烟的姿势不同了。有时,他从鼻孔里喷出烟柱,如急流、飞瀑般下飘;有时,他从嘴巴里吐出烟圈,如旋风、云朵般袅袅上升。而在或飘或飞的过程中,他目光的明亮,照亮了前方不远处的一栋上升的大楼。大楼的升降机下有个姑娘的背影,穿着泥不住的桃花短裙,露出修长的两腿;包着灰不了的桃红头巾,流出飘飘的长发。小伙子是为她哼唱轻快的小调吗?是为她制造着形态生动的烟圈吗?我希望是。但姑娘永远背对着小伙子,只给他一个婀娜多姿的背影可供想像。于是我想,在这样的建筑工地上会有什么美人呢?蒙着泥灰,又日晒雨淋的,不是模样太傻,就是皮肤太黑。姑娘没有转过脸来,这脸一定是太丑了,怕小伙子瞧见了失望。但整个春天,小伙子仍然一日复一日坚韧不拔地望着那边,仍然把烟圈的各种美的图案优雅地吹向天空。我实在忍不住好奇,有一天从学校回来,就骑车直奔姑娘的跟前,从此多次奔到姑娘的跟前。有一次,我找了个借口要买房上楼去看看,就对姑娘的侧影说:“这位小妹,我这单车放在这里没问题吧?我要到楼上看看,这楼的电梯开了吧?”姑娘往升降机里放完了砖头,扭过头来对我一笑,我一时惊呆了。姑娘的脸洁白无瑕,仿佛荡漾着朝霞的水面又融入了明月的皎洁,是那样的妩媚而清秀……一刹那,我感到姑娘的笑容把整个春天的美都浓缩进来了。升降机也是一棵开花的树,注满了春天的诱人气息。姑娘对我说:“单车放这儿吧,我帮您看着,放心吧。电梯开了……”声音就像流淌在阳光下的清泉,荡漾着光芒,且清澈见底。我多想对她说,美丽的姑娘,你背后有一双放射着爱情光芒的眼睛,已像春天的阳光一样,沐浴了你很久呢,你能转过身看看吗?可这时,姑娘又咬紧着牙,忙着给升降机里装进砖头了。升降机像一架无情的溶器,溶掉了姑娘的笑容,也溶掉了建筑工地上灿烂的春天。而他们仍然只是个蠕动的泥人,有时如直立的蚯蚓,有时如地下钻出的土地的神,雨水洗不去他们的泥色,和风抚不平他们的心潮。春天的花香不属于他们,他们只有满身的汗臭与苦楚。夏天来了,人们躲到了树阴下面,施工者仍然在灰蒙蒙的天空下汗流如雨……炎炎的烈日中,高楼继续升高,姑娘仍然只给小伙子一个美丽的背影。而小伙子似乎从不气馁,从春到夏,虽然在打出了一个又一个盛满泥浆的大坑时,没有为自己打出一个可盛爱情的小坑,却仍然执着地打着,执着地哼唱着轻快的小调,蓬松着金色的浓发,吐着烟圈变化出许多新奇的图案,一如既往地眺望着姑娘。我不由想,也许他们早就是一对恋人了呢,只是小伙子把姑娘拥入怀里的时候,没有人看见罢了。他们其实有着常人所没有的甜蜜呢。不然,为什么建筑工地上走了一个又一个施工者,他们仍然还在呢?不然,为什么小伙子仍然在泥浆中泥不掉一腔轻快的小调、满头的金发、无数奇妙的烟圈呢?不然,为什么小伙子总是盯着姑娘的背影,现出梦幻的神情呢?萧萧秋风中,稻麦飘香,瓜果结满了枝头,小伙子青春的枝头结出了什么呢?进入深秋的一个阴霾的午后,我发现小伙子的金发不见了,光头的小伙子一下失去了许多活力,就像秋天的树落了绿叶一样,虽然他仍然哼唱着轻快的小调,吐着生动的烟圈,盯着他永远盯着的方向。我忽然想,这小伙子与姑娘热恋的天空可能也出现了阴霾吧?顺着小伙子的眼光,我再看他前方的时候,不禁大吃一惊:那前方升降机旁装着砖头的人已经不是那个姑娘,而是一个有点驼背、头发花白的人了。别说小伙子,就是我这个已经习惯于望见姑娘的陌生人,对于姑娘在那个位置上的消失也惆怅不已,尽管我知道我的惆怅毫无用处。这建筑工地上的施工者的来去,就像黄土挖起来又埋下去或运走一样,毫无新奇之处,从来不会有人留意一个施工者的出现与消失。因而,姑娘消失了也就消失了。姑娘为什么会消失?姑娘消失的过程怎样?小伙子清楚吗?我不知道,也无法知道。只知道隆冬的冰雪中,大地一片洁白的时候,他们仍然是一身泥黄……但是冬至那天的黄昏,我在附近菜市场旁的一个肮脏昏暗的小巷口,惊讶地发现了姑娘。姑娘与一个男人守着一个补鞋的担子。姑娘正专注地补鞋,男人佝偻着背,仰起一头花白的头发,大口地吧嗒着喇叭筒纸烟。我仔细地看了看,发现驼背的花白头发的脸只残留着一点活气,虽然看不出确切的年龄,但可以肯定,他已经老了,他就是替换了姑娘在升降机旁装砖头的男人。这是怎么回事呢?驼背的花白头发是姑娘的父亲或其他的长辈或亲戚吗?我想直接向驼背的花白头发打听,但他不认识我,我惴惴再三,终于不敢冒昧,只从鞋担边拉过一把小凳子傍姑娘坐下。姑娘抬起头来,很快认出了我,送给我一个仍然妩媚动人的微笑,虽然消尽了先前脸上的容光。我忍不住问:“妹仔,你不在工地上做了吗?”她笑着茫然地望了前方一眼,长长的睫毛里闪过一丝淡淡的阴云,又迅速现出满脸的阳光,转向手中的鞋子,一边扎一边说:“我的腿被水泥板砸断了,不能干了。”她身后的驼背的花白头发恶恨恨地看了我一眼,催着姑娘说:“收档吧……”姑娘对他笑起来说:“你跟谁凶啊?”我有点窘,瞥了那男人一眼,问姑娘:“他是……”姑娘妩媚温柔地转向我说:“他是我男人。”然后又埋头扎鞋。我看见姑娘揭掉了头巾的头发乌黑发亮,梳得十分熨帖端庄,想再多聊几句,但天黑下来了。我在离开了他们几丈远的地方,一腿跨在车上,一腿蹭着地面,悄悄地继续看着他们。我看见男人挑起担子走在前面,姑娘两手撑地,用另一条弯曲的腿奇怪地点地,架起沉重的身体,平举着一条空着的裤腿,跟着男人的背后,艰难地用两只手往前走去。没有了一条好腿的姑娘,比街上的行人矮了约半个身子。我就想,她是怎么砸断了腿呢?建筑工地的老板给她出钱医治过吗?她是如何嫁给了一个驼背的花白头发的人?姑娘不是我的亲戚和朋友,也从没有人对我讲起姑娘的身世与经历。而这一切我是多么想知道啊,可是永远无从得知了。我只知道曾经那么美丽的一个姑娘,而今在一个驼背的花白头发的相伴下,坐在肮脏的黄昏的小巷口,守着一个补鞋的担子,天黑后用两手走回家去……此后不多久,在我家斜前面的升降机旁,我没有再看见那个驼背的花白头发。那楼房已经封顶,以至撤走了升降机,拆除了整栋大楼的脚手架时,我也没有看见那个驼背的花白头发。许多个黄昏,我在菜市场的那个肮脏的小巷口,从此只看见姑娘一个人守着鞋担。那驼背的花白头发与姑娘离婚了吗?或是突然也被砸伤而住院了?或是突发恶病老去了?我不知道,到现在也没有人告诉我,我也没有勇气去打听。我只是想:姑娘怎么能独自挑起鞋担呢?怎么能一个人回家呢?那建筑工地上的小伙子知道了这一切吗?虽然小伙子一如既往地哼着小调、吐着烟圈;虽然他仍然出神地望着这姑娘和老人存在过的地方。3到现在,我仍然不能不想:也许,小伙子不知道这一切,他以为姑娘只是像新娘回了一趟娘家一样,到时候自然就会回来了,他可以等待姑娘的再次出现;也许,小伙子知道了这一切,但他所知道的这一切实在太多了,习惯了,不足为奇了,麻木了,姑娘再悲再惨,他又能怎样呢?生活还得继续;也许,小伙子只是望着那楼,那升降机,姑娘不过是它们身上的一部分罢了。小伙子难以忘怀的,是那一栋又一栋楼的每一块砖头中,融入了姑娘和他的青春、热血和人生。他的爱与恨,已随打桩机的打桩深入了地下;他的魂与灵,已随升降机中的砖头升入了天空。他的生命不过是病人床前的点滴瓶,已经一滴一滴地滴入到高楼的砖缝水泥中。当建筑工地上耸起一栋又一栋高楼大厦的时候,包括小伙子在内的千千万万个施工者已由泥土变为泥水或灰尘,或者埋入地下,或者随风飘向天空不见了。我在他们建起的一栋栋气派豪华的小区的别墅、一家家琳琅满目的广场的超市、一座座鳞次栉比的大街的高楼中寻找他们,却很难找到他们的影子。我的目光与失望,就像河流与溃堤一样,在我无眠的长夜里淹没一切,洪水滔滔……我忘不了一个简单的事实:任何一座令人惊叹的高楼,任何一座辉煌崛起而繁荣昌盛的都市,最初呈现的都是原始的建筑工地。与建筑工地一起埋没或飘落的,不单是施工者绚烂的青春、长流的汗水和坚韧的人生,还有我寻找而失落的目光与长夜里不眠的魂灵。作者笔架飞湖笔架飞湖,教师,广东省“十大书香之家”,网易“第一写手”全国杂文类冠军,笔耕数十年不辍,有文章(诗)百余篇(首)见诸全国知名报刊杂志。责任编辑:疏勒河的红柳、雨菡公众g投稿邮箱:qq.白癜风该怎样治愈白癜风专科医院怎么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