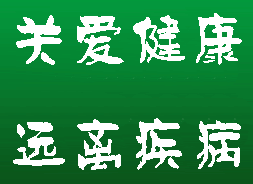就跟那个讲述一个女人陷入自我迷狂意大利电
她
.06.28
如今,她什么都不做,她只写诗,虚掷一个个苍白的故事。
已经是第四百七十八天了,她呆在这个阁楼里,透过窗,望着死去的飞鸟与鲁国故城荒芜的沙砾。
已经是公元后许多年了,鲁国故城的夏天,依旧是沉郁而炙热的,跟公元前一样。这个城市,形形色色的车轮早已抛弃了轨道,车轮上挂着的橡胶替代遥远的木头与青铜。街道依旧车水马龙,人群依旧熙熙攘攘,明朝皇帝的青砖替代鲁国城墙的沙砾,人们只会记得万仞宫墙里沉默的雕像,没有人在乎公元前的繁芜与车马,历史把它们磨平了。
这样沉默闷热的夏天,人们穿着短袖与凉鞋穿梭在这鲁国故地,观光的、生活的,紧急的、缓慢的。只有她,穿着来自西周的缟衣,终日呆在这个阁楼上,蓬头垢面,狂言乱语,与来自西周的沙砾做伴。
如今,她什么也不做,她只写诗。还有一个月,她就毕业了。她实在难以坚持这四年里的最后一个月,难以继续了,她退了学,事关社会的一切让她太痛苦了!
母亲问她为什么,她说她实在太痛苦了,难以忍受,她要死了!父亲逼她回去上学,把她绑到学校门口,她拿起刀子,划向自己的脖颈(那是她最美也是她最喜欢的部位),跪在父亲的面前,哭喊道:“爸爸,求求你了,杀了我吧!”父亲把她一脚踹倒,刀子落在路边,骂道,“你这个逆子!儿子倒想逼死老子了!”随即唾了她一口唾沫,落到她的脸上。她从小受不了脏,心脏一紧张,便晕倒了过去。
她什么也不想做,她只想写诗,有的时候,她连诗也懒得写,仅仅是听凭颅内意识的流动。她也不知道她自己在想什么,上一刻、下一刻。偶尔有句子划过,她就记下来。有时候,甚至握不动笔,她也记下来。总之,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四百七十八天,今天就是第四百七十八天。
这四百七十八天,她时常幻想,也许不止是四百七十八天,也许很早以前就已经开始了,或许早在幼年时代?我们无从得知,只不过这四百七十八天,她表现得极为明显。原谅一个讲述者的无能为力,我终究不是她,没有人会了解一个疯女人的呓语,更何况,一个写诗的疯女人?
我累了,亲爱的读者们,今天到此为止吧。也许你们也不会对这个疯女人的故事感兴趣。可我是多么深爱这个疯女人,她是我的姐姐,父亲打骂她,母亲为她哭泣,她让我的家鸡犬不宁。我也讨厌她,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记下来。总之在童年时代,她就跟别人不一样,我得记下来,哪怕留下一份精神病档案,总之是要记下来。
她是天才,每一滴泪水,都是诗。
.07.03
你好,亲爱的读者们,这个博客,我已经好几天没有更新了。今天终于有时间了。
我的姐姐,近几日发作地越来越剧烈了。有那么好几个午夜,她爬上阁楼的窗台上,狂笑、大哭,嘴边流溢着模糊的诗句。她的声音太微弱,我们听不清,偶尔有句进入我的耳朵,说得好像是什么“穿越时间白色羽毛的沙砾/在公元后没有歇脚之处”,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或许是一首诗里残存的几句,或许只有这么几句。总之我不明白,但我觉得,她是天才,她的痛苦也是上帝送给她的礼物。我姐姐总是念叨,“痛苦,是上帝予我的唯一赠礼”。
我的姐姐,总是会在第一时间记下她唇边流动的呓语。但是有些句子,在不久之后她又会疯狂地撕掉。那个时候,她会哭泣、躁狂,扇自己耳光,还在不停地咒骂自己“我太失败!我太失败!我就该死去,我就该死去!我不要活着如同死了……”
有一次,在午夜,我趁她睡着,偷偷地翻动她的诗,还没有打开,她就醒来了。她拿着刀子刺向我,要我把她的诗集还给她。我害怕极了,哭了起来,她竟把刀子划向了自己的手臂。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翻动她的诗。
上一次,我跟你们提到过,她之前就有这种表征,只不过这近五百天来,表现得日益明显、极端。
她退了学,拒绝一切的社交,拒绝跟一切人的谈话,父母亲跟她说话她都不理。除非她急了,说上一句“让我死了吧!我太痛苦了!”之类的话语。
父亲托人给她找了一个外企的文书工作,工作简单,薪酬尚可。母亲日夜为她焦愁,白头发多了好多根。甚至,恋人,朋友,也被她抛下。她的理由很简单,她要写诗。
她每天只吃面包、黄油,还有清水。她甚至拒绝食物,有时候面包和黄油都令她恶心。母亲煲了她最爱吃的猪蹄汤给她端了过来,却被她摔到了地板上。母亲终于难以抵制自己的痛苦,落下泪来,她却笑了起来。阁楼里除了混了丁达尔浑浊的光束,便是母女俩的哭笑声还有残乱的稿件。
她每日的欣慰便是窗外苍白的桐花,可是早已丧失了花火,夜半时分,蛙鸣也早已停止。除了清晨布谷鸟的叫声,这座房子是寂静而苍凉的。
(最近脑海一直冒出来的场景,算是一个故事吧,也许不符合小说的写法,没有几个小说,只有一个人物的,所以我选择日记体这种投机取巧的方式。更何况是这样一个自燃的人,总之也是最近自己的状态吧!尝试写一个完整的故事,虽然我只知道最终这人是不幸的、陷入自我的迷狂中,但我不知道中间的故事会是怎么样。指望边写边想起来吧。)
北京看白癜风最好专科医院浙江治疗白癜风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