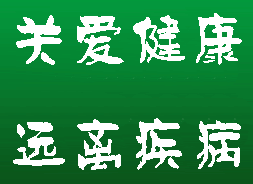曹禺逝世20周年夏志清记录的曹禺早年生活
年12月13日,著作剧作家曹禺因病在北京逝世,今日正好是曹禺逝世20周年。
曹禺曾于年到访美国,与文学评论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志清有过简短的交往。夏志清受邀将曹禺此次到访哥大作一记录,于是有了《曹禺访哥大纪实——兼评北京人》一文。该文后于年被收入《海外学者论曹禺》一书,今天从这本书中摘录此文发布在此。
年,曹禺,北平清华大学。文内图均为新华社资料
4月3日那天华氏七十一二度,真称得上是个“明朗的天”。饭后心境愉悦,大家都愿意走回恳德堂。但怕曹禺劳累,我同张光诚(台湾前辈作家张我军的公子)还是乘计程车把他送到百老汇哥大门口。
二时许我同英君陪着曹禺进恳德堂的休息室,人已坐满了,看样子有五六十位。早已有人为我们安排了三支椅子,我们就坐下,旋即由我介绍曹禺,座谈会开始。
去年钱锺书来哥大,座谈会上只谈学问,因为他过去的生活我们二人私下面谈时,已讲到了不少。我同曹禺交情不够,许多事情不便面问。假如由他一人演讲,他一定又要大骂“四人帮”,大家听了无聊。我想不如让他多讲些过去的生活,给文学史留些资料,写下来大家都可以参考。我有时发问,非常不客气,如问他父亲有没有姨太太?家里有几个人抽鸦片?但这种“逼供”的方法,的确见效,曹禺打开了话盒子,讲了不少真话,至少有一大半是所有现成的传记资料上所未载的。曹禺讲了一小半,自动站起来了,说道从小就是演员,今天即在国外演戏,也得打起精神来,让在座诸位感到高兴。重忆旧事,曹禺讲话的兴致真的提高了。
年6月,曹禺(右)和著名戏剧家、导演焦菊隐参加北京人艺院庆大会。
曹禺原籍湖北省潜江县,但很可能生下来就跟他父亲和长兄住在天津。他们一家四口(曹禺称其长兄为“老哥哥”,想二人年龄相差很大),佣人有七八个。其中一个名叫阿贵,闲着无事做,会画几笔工笔画。《雷雨》里周府上的男仆取名鲁贵,道理在此。曹禺父亲是旧式官僚,天津住宅极大。十三四岁时,曹禺走读南开中学,下午四时放学回家,整个屋子静悄悄的,原来父母亲同老哥哥夜里抽足了鸦片烟,清晨才入睡,那时还没有起床,男女佣人也不便惊动他们。《日出》里那两句名言:“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写的就是曹禺家里实况,曹禺说父亲没有小老婆,不是他不想讨,只因为母亲人比较厉害,不敢讨。《雷雨》里的周蘩漪,《北京人》里的曾思懿都是比较厉害的女人,不知同作者的母亲有无相像之处?
中学期间,曹禺每天同他父母见面的时间至多一小时。晚上他们起床了,他得预备明天功课,不便多同他们讲话。曹禺的童年显然是寂寞的(一个人从小生活太正常,家庭环境太温暖,就不易成为艺术家),他需要淘伴,十四岁就对戏剧发生兴趣,十五岁加入了南开中学的一个剧团,认真演戏。他专演女角,曾扮过《玩偶之家》里的娜拉。谈话间曹禺也提到《一磅肉》这出从莎翁《威尼斯商人》改编的戏,不知鲍西娅这个角色是否也是他扮演的。
我问他最早接触的西洋文学书籍是哪一种,他想了一下,说是林琴南译的《吟边燕语》(即兰姆姐弟所编写的《莎士比亚故事集》)。钱锺书对西洋文学发生兴趣,也是从读林琴南翻译作品开端的。我问曹禺,林译哪几种小说给他的印象最深,他却记不起来了。我中学期间就只读过了一种林译小说《撒克逊劫后英雄略》,深深为之感动,尤爱那位犹太女子Rebecca(电影里由伊丽莎白·泰勒演出,那时她才十八九岁),觉得她的人格真伟大。后来司各特的长篇小说读过三四部,长篇叙事诗也读过一二篇,就不敢碰《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生怕破坏了读中文译本时那种美好的印象。
年秋,曹禺(右二)在北京郊区体验生活期间与干部、社员合影。
曹禺十六七岁,父亲破产身亡,从此家里就穷了。考清华大学的那个暑假,曹禺只身抵北平,住在“朋友的亲戚家里”。此家人姓徐,真是书香门第,有一间书斋的家具都是宋代的珍品。我一直对学生说,宋代读书人的趣味最高雅,看宋版书,墙上挂着宋代名家的山水画,吃饭喝茶都用宋代的瓷器。我在翁同龢后裔家里翻看过宋刻书籍,每在博物馆看到宋瓷碗盏,总是流连不已。纽约有个大收藏家名叫亚瑟·萨克勒(ArthurSackler),据说他卧室里的家具地毯,包括床在内,都是明代制品,已相当了不起了,想不到民初时期竟还有人家日常用宋代的木器。但是徐家的子孙很不上进,从小抽上了鸦片,偷偷地把家里的古玩卖掉。那个暑期曹禺接触到不少败家子弟。写《北京人》的灵感即来自那些旧式家庭,包括自己的老家在内。当时我忘了问曹禺,曾文清是否即是他的长兄?
曹禺同好多人一样,回忆中还是感到大学四年的时光最为甜蜜。但他自称读书不用功,一人在图书馆看杂书,得益最多。他提名讲起的老师就只有英文教授RobertWinter一人。
《北京人》一开头有这样一段描写:“屋内静悄悄的,天空有断断续续的鸽哨响。外面长胡同里传来那时北平独有的单轮水车,在磷磷不平的路上单调地‘吱扭扭,吱扭扭’的声音。间或又有磨刀剪的人吹起烂旧的喇叭‘唔瓦哈哈’地吼叫,冲破了沉闷。”曹禺说从来导演《北京人》的人,不把这些幕后的声音复制出来,增加剧本的气氛,认为十分遗憾。说到这里,曹禺真的模拟了单轮水车的声音,各种北平小贩叫卖的声音,以及深夜瞎子算命先生敲打铜锣的声音,听众都入迷了,七十老人曹禺仍是位好演员,自己也很得意,只可惜“交流中心”给他安排的节目,让他忘不了出差大臣的职责,很少有流露真情的机会。
曹禺和夫人李玉茹(京剧表演艺术家)在一起。
《北京人》里最重要的象征是棺材,我觉得就把它放在小客厅上,每幕都给观众看到,所收的戏剧效果岂不更强?曹禺不以为然,他说一则不雅观,二则象征性的物件不断有人在戏台上讲起就够了。虽然如此说,《北京人》里其他的象征物件——鸽子,剪纸《北京人》的黑影,鸦片烟枪——倒是时常在戏台上出现的。曹禺说当年好的棺材,的确要值美金一万或数万元(我连忙插嘴对听众说,二三十年代的美金一元等于今天的十元)。老人家有时爬进棺材躺着几分钟,自感非常得意。他们买了寿木,一年一年加漆,主要怕子孙不孝,断气后连一口好的棺材都不给他们买。
读完《北京人》,我就挑《日出》来讨论,此剧正在纽约上演,而且上过我“中国现代文学”这门课的学生,都已读过译本。大家都知道,曹禺写他的早期名剧,受奥尼尔、易卜生、契诃夫,以及希腊悲剧家的影响最大。但他在清华读书期间,想来好莱坞电影也看了不少,无形中可能受了些影响。《大饭店》年发行,是当年金像奖最佳片,嘉宝、巴里摩尔兄弟,琼·克劳馥、华莱士·比里等明星主演,当年中国洋派大学生没有人不看的。年,米高梅公司又推出一部全明星阵容的巨片《晚宴》,主演人是巴里摩尔兄弟,珍·哈露、华莱士·比里,老太婆玛丽·杜丝勒等。《大饭店》讲柏林“大饭店”内几个住客二三天内的故事;《日出》故事推展于天津大旅馆交际花陈白露的套房内,进进出出的都是她那些朋友们,贫富不等。她最主要的阔朋友是潘月亭,有位已解雇的小职员黄省三不时进旅馆来找潘经理同他的助手李石清。《大饭店》里工厂老板华莱士·比里在旅馆里见到那名业已解雇的老职员里昂·巴里摩尔,其态度之恶劣,简直很像李石清。《晚宴》里面有位失意的百老汇舞台明星约翰·巴里摩尔,最后同陈白露一样,债台高筑,一无出路,在他旅馆房间内煤气自杀(陈白露则服安眠药片)。我问曹禺这两部片子,对《日出》的写作有无借鉴之处。这样一问,曹禺有些急了,《大饭店》电影没有看过,书是看过的(原是Vicki.Baun写的德文小说),毫无影响。其实,《晚宴》未搬上银幕前,当年也是百老汇名剧,由GeorgeKaufmann同EdnaFerber二位红作家合编。抗战期间,李健吾把它改编成一出中国背景的话剧,取名《云彩霞》,我曾在上海看过。
年,曹禺工作之余看书。
我再问,陈白露流落风尘前,曾同一个诗人结过婚,这位诗人“最喜欢看日出,每天早上他一天亮就爬起来,叫我(白露)陪他看太阳”,给我“生铁门答尔”的感觉。世上诗人不多,陈白露没有这段结婚经验,是否更真实些?曹禺说,不一定写诗出了名的才是诗人,像陈白露丈夫这样为理想而活着的青年当时多得很,一点也没有什么不寻常。曹禺对陈白露极端偏爱——他说她是极聪明、极有勇气的女性,就是社会害了她。(曹禺说自杀也需要勇气,他们——指听众——失意时敢自杀吗?)福楼拜曾说过,“包法利夫人就是我”;看样子,陈白露也是曹禺自己的写照。至少“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死了,家里更穷了”这两点是完全相同的。
年,曹禺观看年轻演员重新排练演出的《北京人》后与演员、导演交谈。
曹禺讲自己早年生活,讲两出戏,早已超过一小时了。下午还有别的节目,他不想再说什么了。我说谈谈新戏《王昭君》罢,这样又多讲了十多分钟。曹禺说《王昭君》是周恩来示意要他写的,但不能算是“奉命文学”,因为他自己对王昭君此人也极感兴趣。中国古代四大美女——西施、昭君、貂蝉、杨贵妃——要算她最伟大,对中华民族的贡献最大。她“和番”之后,汉人同匈奴人保持了六十年的和平,这是不容易的。为了写此剧本,他曾到新疆、内蒙古去考察过。很多人骂他不应改写古老的明妃传说,但他认为《王昭君》是按照史实写的,虽然“戏没有写好”。主要原因,昭君同单于结婚之后,编起戏来,“办法就少了”。明年《王昭君》要拍成电影,他已示意编剧人原剧有两三处可以改编,将来电影在纽约上映时,请诸位多多指教。讲到这里,座谈会看样子要结束了,我再问曹禺一个问题:是否在从事新剧本的写作?他说是的,但写的是什么题目他坚决不肯透露,是今装戏还是古装戏,他也不肯说一声。他说这不是卖关子,题目一旦泄露了,人家要问个不休,自己也不能定心写作了。
年,曹禺和挚友巴金在一起。
同一天晚上我开始写这篇报道,写到星期一(4月7号)清晨,初稿差不多写好了。下午起床后,到恳德堂去走一遭,因为通常星期一信件最多。不料在系办公室里竟看到了曹禺留给我的一本书,一件礼物。书是我极想一读的《王昭君》,卷首有作者近照,该页上新加了题字:“C.T.夏教授教正。曹禺,四,五,纽约”。礼物是一只浅绿色的小象,看来是由一块雪花石膏雕刻而成的,非常晶莹可爱。曹先生虽然记不清我的中文名字(所以称我为“C.T.夏教授”),显然对我不无好感,临走前还托人带给我一本书,一件礼物,真的很为其友情所感动。先在这里道一声谢,并祝他在访游美国期间,珍摄身体,多多保重。
也正巧,同天收到了香港黄维梁弟寄来的一包书,其中有本巴金《随想录》第一集(年香港出版)。回家把该书浏览了一遍,发现其中有一篇《“毒草病”》是专讲曹禺的,还引了一段巴金写给曹禺的近信。这段信里的话我想也写出了海内外读者寄予曹禺的厚望,不妨引之以结束全文:但是我要劝你多写,多写你自己多年来想写的东西。你比我有才华,你是个好的艺术家,我却不是。你得少开会,少写表态文章,多给后人留一些东西,把你心灵中的宝贝全交出来……
,4月19日完稿
《海外学者论曹禺》,田本相邹红/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年5月。
本文由澎湃新闻臧继贤编辑,可点击阅读原文查看。
赞赏
长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