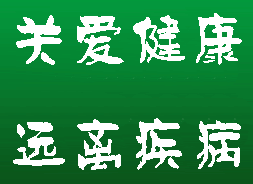幸福,是不是永远不会到来
点击?播放,音乐响起,阅读开始了?
一个女人为生活、家庭、爱情所困,选择去死。奔赴天堂的路上,遇到上帝,这是她与上帝的对话:
“我找不到出路。”
“但这就是出路吗?”
“这样至少用不着选择,我为选择以及无法选择都感到疲惫。”
“你不能忍一忍吗?”
“我无法安于现状,却什么都无法改变。”
这是柳·彼得鲁舍夫斯卡娅《幸福的结局》一文中的段落,现在我们来读这位俄罗斯女作家另一篇。
这儿
heyzher
发现世界另一种可能
﹀
安排生活
文丨柳·彼得鲁舍夫斯卡娅
译丨陈方
有一个年轻的寡妇,虽然也不太年轻,已经三十三岁甚至更多,这些年间,总有一个离了婚的男人来找她,他是寡妇的丈夫从前的一个熟人,他不是随随便便地来的,而是想在这儿过夜,事情就是这样的。但是寡妇不让他留宿,有时候说没地方,有时候是别的借口,总是拒绝。男人诉苦说膝盖疼,说时间太晚了。他总是带一瓶葡萄酒来,寡妇趁男人独自喝酒的时候安排孩子睡觉,切一点平常的、手头就有的蔬菜,或者煮一个鸡蛋,简而言之,她忙碌着,但不是特别用心。男人总是长篇大论,眼镜片发亮,他是个有点儿奇怪的人,懂两门外语,但经常在夜里给单位打更,有时候还看管暖气,不过都是在夜里。他一点儿钱都没有,可还是有一个规矩——他找人去借很少一点钱,人于是就变得轻松自如了,他给自己买一瓶酒,之后抱着酒瓶,清醒地认定自己无论在哪儿都是一个受欢迎的客人,尤其在拥有一套舒适住房的朋友的遗孀那儿。
男人就是这样做的,他一本正经地从那儿离开,丢下自己的酒瓶,清醒地思量着他自己现在的价值,尤其是对于这个孤独的女人、这个寡妇的价值。寡妇总是给他开门,不忘他曾经是丈夫的朋友,而丈夫以前总说萨尼亚是个好人,可就因为这样,丈夫活着的时候萨尼亚好像很少出现在地平线上,基本只是在类似婚礼这种所有人都让参加的大型活动中才有他,而生日和其他诸如新年之类的活动肯定没人叫他,更不用说偶尔的晚间聚会和喝酒聚餐了,那是他们生活中最好的东西,他们一直聊天到早晨,此外,他们互相帮助,一起在农村过夏天,孩子之间的友谊也是从那儿开始的,还有孩子们的节日,那是一种有各种各样快乐事情的生活。所有这些事都没让萨尼亚参加,因为他虽然有学数学的人的聪明头脑,还懂几门外语,可是每次都醉得不成样子,之后就开始大声地胡说八道,震耳欲聋地自言自语,无止无休地大喊或者唱歌,最终男同胞们采取行动,顺着楼梯把他撵走。他自己并不知道他是怎么了,后来好像从大家的视野中消失了,他娶了人,是从很远的地方把妻子带来的,住的也是很远的郊外,他当了初级研究员,有了孩子,似乎开始了新生活,当家作主,关于他的消息越来越少,可是突然就打起了电话。
他给这个打,给那个打,纠缠不休地要跟人家说话,好吧,之后或者借钱,或者直接带一瓶酒就去别人家,去有孩子和女人的温暖小窝,他拿着酒瓶就像一个侵略者,别人不欢迎他,所以他就成了侵略者。
要是别人愿意他去,邀请他,让他坐下,劝说他,他也许会安静下来,可能还会说些有用的东西,甚至还会沉默一会儿,甚至还会为自己掉些眼泪,因为很显然,妻子如今也在往外赶他,他的魅力没有了,这个高大匀称、戴着眼镜的首都居民和知识分子,他的英语和德语,他受的大学教育和大学的熟人圈子都没有了。而她是一个从偏远地区来的普通女性,做着普通的教师工作,她显然成熟了,明白了自己可怕的处境,普通妇女很快就能明白一切,于是她也开始往外赶他。
于是所有类似“家庭就是堡垒”这样的谚语带给人的希望全都破灭了,要知道对这个年轻人来说剩下的只有这些东西了,房子和家庭,房子和孩子,房子是自己的,床是自己的,孩子是自己的!
孩子是自己的,不是别人的,他张开小嘴听别人说话,他乖乖地吃饭,去你给他做的小床上睡觉,他在睡觉前拥抱你,像小鸟、像小鱼一样紧紧贴着你,他就喜欢自己的爸爸。
可是妻子马上就像老虎一样现身了,她不允许醉酒的父亲跟孩子亲近,这就是一个难题,她把他们分开,大声嚷嚷着一些显然很耳熟的老话,说你不给家里挣钱等等。萨尼亚说,你跟你妈妈学会了叫嚷,妈妈给她开辟了一条路。
这算什么生活!
于是萨尼亚走了,这并不奇怪,他离开了自己的小城,去哪儿呢,去了首都,在这儿,从前的历史又一次重演,即使在这儿也没人接纳他。
还不错,他彻底辞职离开了妻子,完了,一切都结束了,他离开小城,给自己在莫斯科找到一份工作,在一个暖和的地方当锅炉工。
于是他所习惯的那种生活就开始了,他看来也是为这种生活而生的,虽然他出生在一个有着严格规矩的正统家庭,小时候还总是优等生。
但理智和心灵,我们发现,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一个人有可能是大傻瓜,但却有一颗踏实的、坚强的心灵,那么所有人都会尊重你,你甚至能成为我们国家的首脑,就像曾经发生过的那样。
你也可能生来就是个天才,但却有颗不踏实的、轻浮的或者空虚的心灵,于是就会落得身无分文,就像不止一次在我们的天才作家、画家和音乐家身上曾经发生的那样。
这个萨尼亚恰好就是某方面的天才,但是单位里没人接纳他、理解他,干活的时候他永远钻的不是地方,时间不对,计划不对,不对领导的心思,抛头露面,不懂分工,之后他就彻底甩手不干了,这下子他的第二条(在家庭之后的)可能的退路也没有了,他无法用自己的工作吸引别人,让别人明白他在这个世界上的角色、作用和天赋。
不,崩溃了,消失了,谁都不感兴趣,谁都不帮忙,谁都不需要他的劳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事情,他没找到盟友。我们倒要问问,好撒谎的大嗓门怎么可能有什么盟友呢,他大声说的也许是正经事,就像奥库扎瓦歌里唱的,他小心地暗示、而不是直截了当地唱道,军官的女儿是不会瞧上士兵的。
而如果没有盟友,即使最大的天才也什么都不是。
每个人都至少有一个拥护者,所有的天才都有,哪怕那是他们的兄弟,哪怕是母亲——他们的天使保护神,哪怕是为你做饭的朋友,或者是情人,或者完全是由于同情而开门留宿的不相干的老太婆,但是萨尼亚没人可怜。
萨尼亚找到了立足之地,在那些如此不整齐、不坚强的人中间,在锅炉房、医院的工人中间,在钳工、修理工和打更的人中间。
他们的时光是昏暗而又隐蔽的,谁都看不见,夜里所有人都睡觉,而非人们则走路、闲逛、去买酒、聚会、喝酒、大喊大叫着他们的无聊话、打架,甚至丧命——在那儿,在下面。
他们所有人都曾经拥有一切,可那些东西全都不见了,只剩下了这些,酒瓶和朋友,萨尼亚也是这样,有时候他不跟他们睡在一起,之后他洗干净,在水笼头下洗一洗,起床的时候整整齐齐的,戴着眼镜,胡子刮得很干净,他们地下室的所有人都把刮胡子当成自己的职责,他们看不起大胡子,是啊,就连地下室的工作都不要蓄大胡子的,看来人们会觉得既然连胡子都不能刮,那么显然阀门也转不动,管子也堵不住,可能是彼得一世的遗训,对干机械和仪表盘的大胡子不信任。
萨尼亚刮好胡子,洗好脸,镜片后的眼睛因为不由自主的湿润而闪闪发光,他开始按自己的规矩打电话。
比如,他给那个寡妇打电话,说他会过去。
她推辞。他们所有人都推辞,有什么法子呢?
于是他采取另外一种方式——直接按门铃。
寡妇打开门,而她身后站着她的母亲和孩子。
又能如何呢,门已经打开了,萨尼亚一边往门里走一边宣布他是坐出租车来的,问她们有没有多少多少钱,钱数一直精确到戈比。
年轻的寡妇犹豫不决,她自己也身无分文,她想,干嘛要坐出租车来她们这儿呢,有什么可着急的,但老母亲像准备好了一样开始在口袋里摸索,虽然没找到需要的那么多钱(萨尼亚要的是正好多少多少钱,最后两位数似乎是47戈比),但他还是把所有钱都接过去,彬彬有礼、动作优雅地侧身出去,精神抖擞地走向电梯。
过一阵出现了一个新景象——十五分钟后,萨尼亚拿着酒和蛋糕又回来了。
寡妇浑身冰冷,这意味着萨尼亚要在这儿待一整晚,但是老母亲非常满意,甚至还对带来蛋糕和酒的男人的样子感到开心和激动,她心里泛起了一些快乐的联想。
老太太不住在这里,她有自己的小窝,而且,多巧啊,她也有一颗同样轻快的心灵,轻快而不安定,常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大吵大嚷,流眼泪,她善良,某些时候还不记仇,她能把什么都献出去,送出去,她是神圣的,随时就到随便什么人家去,她有一颗朝圣者的心灵。
她仅在外表上是个老太太,是个外婆,而内心是个永远的流浪汉,她反复无常,她自己的一切都随身带着,所有的煤气费、水费的账单都带着,此外还有悠远的、深深的忧伤和孤独,还有对光明和温暖的渴望,她一收拾好就去女儿那儿。
而女儿心慌意乱,因为老太太显然逐年变得坐不住板凳,爱唠叨,操着检察长的腔调,说所有人都把她抛弃了,她提要求,诅咒人,而事实上她需要有人给她饭吃,给她穿衣戴帽,给她洗澡,让她暖和,照顾她睡觉,她是个老小孩,是个彻头彻尾的孤儿。
因此,一套房子,一个厨房,一个带小孩的女主人,还有这两个孤儿,他们激动地坐等别人给他们弄吃的。外婆满脸红光,别人不怎么邀请她去过节,这不知怎么已经成了规矩,而她自己去,节日对她来说就是一切,就是生活的全部意义。
酒瓶打开了,鸡蛋煮好了,圆白菜切好了,土豆也开锅了,两个逃亡者的眼镜闪闪发光,只不过萨尼亚是近视,酒瓶底那么厚的镜片后面眨着浮肿的小眼睛,而外婆的眼睛在有放大作用的镜片后显得又大又亮。他们的焦点是饭桌、灯光、温暖,有人给他们服务,像对正常人那样对他们,外婆开始和萨尼亚进行一场她觉得严肃的、甚至关乎命运的谈话,她问他是否结婚了,之后搞清楚他全都结束了,离婚了。那又怎样呢?外婆显然是这样想的,她一直喜欢女儿那些来自半城半乡的熟人,他们对她很好,彬彬有礼,按老规矩首先是对妈妈讲礼貌,他们那儿就是这样的,尊敬老人,刮胡子,戴领带,讲究一些规矩。之后萨尼亚给所有人倒酒,趁外婆像小姑娘那样用嘴唇抿酒的时候,女主人分身去给女儿讲睡前故事,把洗衣机里的衣服掏出来,突然,电话响了,这时瓶子已经见底了,萨尼亚已经在震耳欲聋地给外婆讲他最近得知的所谓新闻,他喜欢一些奇怪的事实,他可是天才啊,他读过很多书,现在想编一本字谜书,他知道别人会为字谜书花多少钱,他极其需要钱,但是他还需要,还需要一台电脑,他是有计划的——想在计算中心找一份夜间工作。乌拉!外婆认为,她的脑子里闪过一道亮光,她觉得她现在能为自己孤独的女儿安排生活了,而女儿这时正在和那个她亲近的人打电话,小孩子大喊着让她继续讲故事,结果外婆来到走廊里的电话旁,就像她觉得的那样,像母亲那样诚恳地说:
“快点打,你怎么回事,已经在这儿聊了半小时了,大家都等着吃东西呢。……孩子正在哭,你真是的。”
而女儿听不见那个让她感到亲近的人在说些什么,他们谈了很久,陶醉地说着那些生产问题方面的话,还有什么人的论文,话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语气。
“你怎么回事,”外婆说,“在这儿跟我嘟囔什么,吃饭时间到了!土豆已经好了。该吃饭了。去给孩子讲故事!时间晚了,别说了!他要走了!”
这个场景是这样宣告结束的——萨尼亚还坐在那儿,而且相反,一点儿都不想走,“就让他在这儿住一宿吧!”外婆感叹道,她也不想步履蹒跚地回到她那个冰冷的老人窝去,她们给萨尼亚在厨房铺了一张折叠床,等待外婆的是沙发,女主人要在充气气垫上睡一夜,但是萨尼亚还在一边高谈阔论一边抚摸着病膝盖,他不想睡觉,因为夜晚就是他的王国。
然而所有人都躺下了,灯熄了,冰箱就像小溪一样潺潺地响,天花板上像扇子一样稀疏地散射着过往夜车的灯光,流亡者和流浪汉们幸福地睡着,小姑娘轻声地打着鼾,她显然又要开始感冒了,又得陪着生病的孩子,不能去上班,要是把外婆留在家里,女主人躺在地板上想,那就是接连两个星期的焰火表演,吵嚷,流眼泪,指责,可是怎么办呢?
而那两个人觉得一切正常,他们在暖和的家里,他们终于找到了母亲,可以从头开始生活,一切都像在正常人那里一样,干净,家庭,节日,接连不断的节日,饭桌上的馅饼,有个人会决定所有的事,一切都会像他说的那样,没有害怕,没有孤独,然而女主人在地板上听着孩子的鼾声,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
END
点击标题,直达阅读:
萧红书信集:别人的黄金时代,是舒展着翅膀;我的黄金时代,是在笼子里度过
↑点它
治疗白癜风的有效偏方北京治疗白癜风最好的专科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