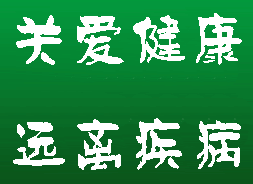有关移情爱的评论德文译出
每一个精神分析的初学者一开始无疑害怕某些困难,他们必须解释病人的自由联想,并处理压抑的衍生物。但是,这些困难很快变得微不足道。他们转头发现,在移情的处理中他们将遭遇绝对真实且严重的困难。
从相关的情景中,我选择了一个独特的,简要素描性的例子。不仅是因为它的频繁出现和它的现实意义,也是因为理论的需要。
我设想的情景是,一个女性病人通过直白的暗示使他人猜测到,或自己直接表达,她如一位俗尘中的女子那样,爱上了给她进行分析的医生。这种情形有其痛苦、滑稽而又严肃的面向。它错综复杂,含义多样,无法避免又难以解决,以致于相关的讨论长久以来并未满足分析技术上的强烈需要。
我们可以嘲笑他人的错误,但是,我们自己并不是总能免除同样的错误。因此,我们力争解决这一难题的努力至今未获成果。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总是重复遇到医生的谨慎性职责,这一职责在生活中不可或缺,但在科学研究中却没有必要。
精神分析的文献也源自真实生活,这里就产生了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近来,面对这一职责,我把自己摆在另一位置上,并进一步说明,所谓移情情境为何让精神分析治疗的发展在前十年里停滞不前。
对于受过良好教育的外行人来说(此类人也许对应的是精神分析所谓的理想的文化人),与爱相关的事情不能和其他的事情用同一标准来衡量。它们似乎存在于某一特殊的页面上,没有其他的描述可以匹配。
当女病人爱上她的医生,外行人会认为,只有两种结果存在。极少的结果是,所有情况都允许两者在法律上持久地结合;通常的结果是,医生和女病人分开,原本已开始的为病人提供康复的治疗就好像因为某种自然灾害的破坏而终止。
肯定还有第三种结果可以设想,那种非法的,不求永恒而真实的爱恋关系的联接看起来可以和后续治疗相匹配。但是,市民道德和医生之尊严将使这种情况成为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毕竟,外行人希求分析师尽可能明确的保证,让第三种情形悄然终止。
清楚的是,精神分析师必须用不同的立场来看待事物。
让我们考虑第二种结果中我们描述的情境,当女病人爱上医生后,她和医生分开了,治疗被终止。但是,女病人的情况使得她急需寻找另外一个医生,在那里重新进行分析。同样的事情将再次发生,病人感觉又一次爱上了她的医生。当她再次中断,然后找到第三个医生重新开始,如此类推。这一确证了的事实(众所周知,这是精神分析理论的基础)可以提供两种价值,一个是对执行分析的医生的,另一个是对需要分析的女病人的。
对于医生来讲,它意味着一种宝贵的启示,以及一种在医生身上可能存在之反移情的警示。他必须认识到,病人的移情爱是由分析情境诱发出来的,而不是因为他的个人魅力使然;他没有任何理由对这种在分析之外称之为“征服”的感受志得意满。提醒自己记得这个总是有益的。对于病人来讲,她只能在两种可能中选择其中一个:要么放弃精神分析治疗,要么遵从无法逃脱的命运而爱上她的医生。
我并不怀疑,女病人亲属将选择两种选择中的第一个,就如分析师将选择第二个一样。但是,我认为,这种情形不可听任家属出于关爱的,或者甚至是自私和嫉妒的考虑而做出的决定。只有病人的利益才具有决定性。亲属的爱是不能治愈神经症的。
精神分析师不必被迫地接受对病人的分析,但是他可以承担某种有效的,不可或缺的功能。那些作为亲属,采取托尔斯泰式态度对待此类问题的人,如果想不受干扰地拥有他的妻子或女儿,那么他们必须承担这样的结果:她将保留她的神经症,以及她爱的能力的相关障碍。这最终就像一次妇科治疗。
另外,当嫉妒的父亲或丈夫认为,他们的女儿或妻子应该脱离对医生的爱恋时,以及当他们让她选择另外一种类似分析治疗的办法来治疗她的神经症时,他们将产生巨大的误解。最终的结果必将是,确实存在的爱恋将保持不被表达和分析的状态,任何对疾病治疗的努力也绝不会出现,病人将重复进行分析。
据我所知,某些运用分析的医生经常期待病人爱的移情出现,甚者,提出所谓“只有爱上医生,才能让分析进展”的观点。我不能想象出一个比此更无意义的技术了。医生如此做,将剥夺了这一现象中具有说服力的自发因素,为自己设置难以消除的障碍。
首先,肯定不会出现移情中的爱对治疗产生有益作用的现象。那些即使是最顺从的女病人突然间将失去对治疗的理解和兴趣,她们想谈论和听到的都只有爱情,并希望得到回应。她们中途放弃了或者忽视了她们的症状,是的,她们声称自己已经好了。分析的情景完全发生了改变,一场游戏被突然出现的现实状况打断,就像在戏剧的演出中火警声突然响起。第一次经历这种情况的医生并不能轻松把握分析的局面,很容易被假象迷惑,错误地认为治疗可以结束了。
伴随一点点的反思,人们可以找到自己正确的位置。首先,我们应该考虑,所有阻碍治疗进程的事情都可能是阻抗的表现。毫无疑问,在暴风骤雨般对爱的渴求中,阻抗占据了很大一部分。医生很早就能够察觉病人含情脉脉移情的征兆,而病人的驯良,对分析解释的接受,非凡的理解能力以及显示出来的高智商,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归因于她对医生的态度。现在,所有的都烟消云散,病人完全失去了理智,她看起来被她的爱所吞噬。这一变化很有规律地在某个节点上出现,而恰在此时,医生必须要求病人承认或者回忆她生命历程中被压抑的痛苦而艰难的片段。分析中的爱恋一直存在,在它表达之时,它开始成为分析中的阻抗,阻碍治疗的进展,转移所有分析中的焦点,让分析师处于尴尬的困境中。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在这种情境中存在复杂动机的影响。这些动机中,一部分是让爱恋发生连接,另一部分是阻抗的特殊表达。第一种情况下,女病人努力确证自己身不由己,通过把医生降格为情人来打破医生的权威,并且觊觎那些爱恋满足中的继发获益。从阻抗的角度来讲,我们可以假设,阻抗偶尔用爱的表白作为一种方式来试探分析师:在它顺从的情况下,它将不会面临斥责。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有这样的印象,阻抗就像一名奸细(agentprovocateur),煽动爱的火焰,鼓吹性欲臣服的意愿,由此,冒着有失教养的危险,愈发促使压抑的实现。所有的细节可能在单纯的案例中不会出现,不过,正如我们所知,阿德勒在此之前把这些视为整个过程的根本部分。
据我所知,某些运用分析的医生经常期待病人爱的移情出现,甚者,提出所谓“只有爱上医生,才能让分析进展”的观点。我不能想象出一个比此更无意义的技术了。医生如此做,将剥夺了这一现象中具有说服力的自发因素,为自己设置难以消除的障碍。
首先,肯定不会出现移情中的爱对治疗产生有益作用的现象。那些即使是最顺从的女病人突然间将失去对治疗的理解和兴趣,她们想谈论和听到的都只有爱情,并希望得到回应。她们中途放弃了或者忽视了她们的症状,是的,她们声称自己已经好了。分析的情景完全发生了改变,一场游戏被突然出现的现实状况打断,就像在戏剧的演出中火警声突然响起。第一次经历这种情况的医生并不能轻松把握分析的局面,很容易被假象迷惑,错误地认为治疗可以结束了。
伴随一点点的反思,人们可以找到自己正确的位置。首先,我们应该考虑,所有阻碍治疗进程的事情都可能是阻抗的表现。毫无疑问,在暴风骤雨般对爱的渴求中,阻抗占据了很大一部分。医生很早就能够察觉病人含情脉脉移情的征兆,而病人的驯良,对分析解释的接受,非凡的理解能力以及显示出来的高智商,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归因于她对医生的态度。现在,所有的都烟消云散,病人完全失去了理智,她看起来被她的爱所吞噬。这一变化很有规律地在某个节点上出现,而恰在此时,医生必须要求病人承认或者回忆她生命历程中被压抑的痛苦而艰难的片段。分析中的爱恋一直存在,在它表达之时,它开始成为分析中的阻抗,阻碍治疗的进展,转移所有分析中的焦点,让分析师处于尴尬的困境中。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在这种情境中存在复杂动机的影响。这些动机中,一部分是让爱恋发生连接,另一部分是阻抗的特殊表达。第一种情况下,女病人努力确证自己身不由己,通过把医生降格为情人来打破医生的权威,并且觊觎那些爱恋满足中的继发获益。从阻抗的角度来讲,我们可以假设,阻抗偶尔用爱的表白作为一种方式来试探分析师:在它顺从的情况下,它将不会面临斥责。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有这样的印象,阻抗就像一名奸细(agentprovocateur),煽动爱的火焰,鼓吹性欲臣服的意愿,由此,冒着有失教养的危险,愈发促使压抑的实现。所有的细节可能在单纯的案例中不会出现,不过,正如我们所知,阿德勒在此之前把这些视为整个过程的根本部分。
尽管出现了爱的移情这一困境,如果分析师决定克服此种移情,并坚持将治疗进行下去,为了避免失败,他将如何行动?
在此,我可以简单地以强调普世道德标准的方式假设,分析师能够从不或绝不接受或回应指向他的爱恋。分析师必须视此时为关键时刻,应把道德上的要求和放弃的必要性摆在这个爱上他的女人面前,同时,他应成功地让病人放弃她的欲求,压制自我的动物性部分,使分析继续前进。
我不期望上述第一种抑或第二种期许得以实现。不期望第一种期许实现,是因为我并不是为病人写下这些文字,而是为那些和困难斗争的医生们。同时,也因为我在这里追溯道德规定的起源,即所谓的权宜主义。我很乐意通过对分析技术的考量去除那些“道德附加税”(moralischeOktroi),同时不改变分析的结果。
我将更坚定地拒绝含义不清晰的第二种期许。如果迫使病人压抑本能,放弃和升华,就在她们承认自己的爱恋移情时,医生的治疗瞬间变成了无意义的行为,而非分析的。这就好像是,某人用魔咒将地狱幽灵强制召唤上来后,不问姓甚名谁,重新发回原地。也好像是,某些人把压抑的内容唤起到意识中,仅仅为了将恐惧重新压抑。我们不应该被这一过程的成功所欺骗。众所周知,对于激情,使用崇高的套话经常是文不对题的。病人为此只会感到被蔑视,也不会错过报复的机会。
同样,我也不太可能建议让某些人感觉特别聪明的折中方案,这一方案主张回应病人温存的感情,同时回避所有身体上的接触,直到医患关系能够驶入平静的道路,并上升到更高的层面为止。我反对这种方案,因为精神分析的治疗是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之上的,其中存在着某种教育性的作用和伦理价值。偏离这一基础是危险的。谁熟知了分析技术,他就会在医生面前避免不必要的谎言和伪装,并且为了达到最好的目标,会让自己说出实情。
医生对病人有严格真实性的要求,如果医生自身偏离了真理的方向而被逮个正着,那么医生将把他的权威性置于困境中。另外,尝试在温存的感情中逐渐接近病人,并非完全没有危险。我们的自我控制能力没有那么的好,以至于可能在某一天我们突然间前进得比我们预计的要多。因此,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拒绝中立(Indifferenz)的态度,这一态度是通过压制我们的反移情而获得的。
我已经让大家猜测到了我的观点,分析技术要求医生拒绝满足需要爱的病人的索求。治疗必须在禁欲(Abstinenz)下进行。在此,我并非指单纯的身体的禁欲,也不是要剥夺人的所有欲求,或许没有病人能够忍受这些。我想要做的是建立一个基本原则,我们可以让病人的需要和渴求作为工作和改变的驱动力量而存在,而且必须避免这些需求通过替代物或其它方式得以满足而趋于平息。我们不能够提供其他所有的替代物或方式,因为病人基于她的状态,只要她所压抑的东西没有得以消除,真正的满足就不会实现。
让我们承认,分析性治疗应该在禁欲下进行这一基本原则,应该就文中提到的个案进行进一步分析和深入讨论,由此对该原则可操作性的限度进行定义。但是,我们希望避免这样做,使我们尽可能地接近我们事先假设的情境。当医生表现出不一样的反应,并且利用双方的自由来回应病人的爱,满足她们情感上的需要时,会发生什么呢?
如果医生做如此的估计:通过他的某些迎合,他将确保对病人的把握,病人也会完成治疗任务,从而获得神经症的持久的解脱。经验一定会告诉他,他的估计是错误的。病人将达到她们的目的,而他自己却不会。在医生和病人之间只是重新演绎了牧师和保险代理商的有趣故事。一位不信神的保险代理商重病卧床,家人为他请来了一位牧师,希望他能够在死前皈依。谈话持续了很长时间,以至于等候的人们希望一点点增加。终于,病房的门打开了。那个无神论者没有皈依,而牧师去买保险了。
如果病人发现她的求爱得到了回应,这对她来讲是一种巨大的胜利,而对治疗来讲则是完全的失败。她成功地达成了所有病人在分析中努力追求的目的,她在真实生活中重复了那些记忆中应只作为精神材料重现的和在心灵领域存在的内容,她成功地见诸行动了。在爱恋关系的进一步过程中,她将把情欲生活中所有的压抑和病理性反应带到台前,而且不存在去修正它们的可能,也不会伴随着懊悔和日益加重的压抑倾向,终止她痛苦的经历。这种恋爱关系使分析过程中的影响力得终结;两者的结合是很不合情理的。
同时,满足女病人爱的需求和压抑它们一样对分析来说,都是灾难性的。分析师采取的是另外一种方式,真实的生活不会为此提供某种范本。分析师应避免从爱恋移情中抽离出来,转而去恐吓它,或者去挫败病人。同时,分析师应坚定地节制任何对爱恋移情的回应。分析师应牢牢的抓住爱恋移情不放,视它为某种非现实情境。治疗应在这种情境中得以持续,回溯移情的无意识起源,并且必须协助病人把她们最隐秘的爱恋生活带到意识中,同时掌控住它们。分析师越是让病人感觉到他自己能够抵制任何的诱惑,就越有可能在这种情境中提炼出分析的内容。此时,病人的性压抑还没有解除,只不过被推到了背景中。之后,当病人感到足够的安全,她将把所有爱恋的先决条件、所有性欲渴望的幻想以及所有痴情的细节特征一一呈现到背景前。然后,以此打开通往她爱恋的婴儿期基础的道路。
某一类女性为了分析工作,试图保持爱恋移情,而不去满足它,这样的分析不会获得成功。这些怀抱自然冲动的女性就像孩童一般,无法接受替代之物,不愿意用心灵来取代物质,正如一位诗人所说的那样,她们秉持的是“饺子的理由作为汤的逻辑”。在这类女性面前,人们的选择是:要么回报她们的爱,要么承接被抛弃女人的全然恨意。分析师在这两种状况下不能保证治疗的意图。分析师必须全身而退,白癜风养生北京治疗白癜风医院地址